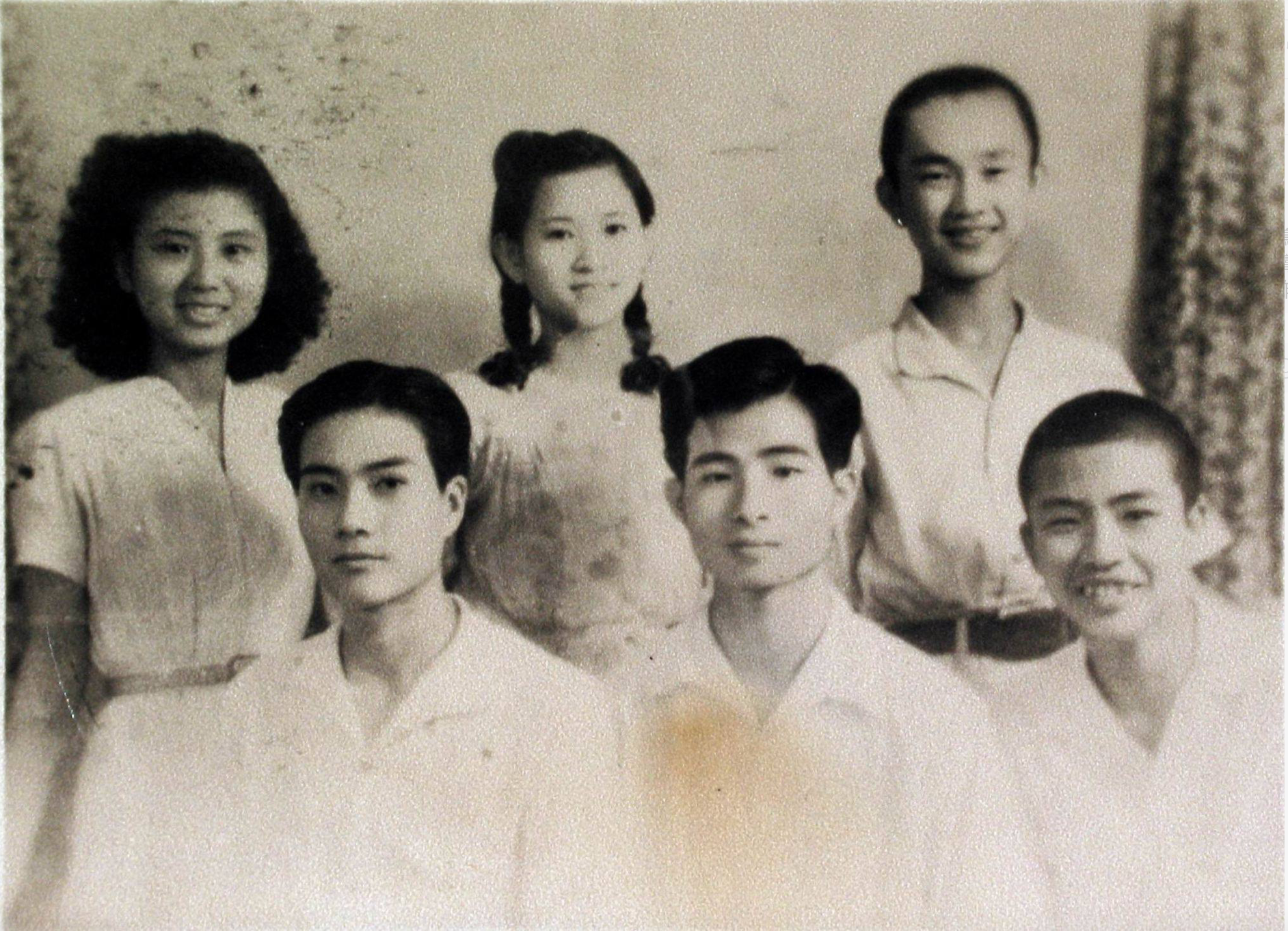死亡的月份過了嗎?……以及一些思絮
五月三十日我在臉書貼出一篇小文,起頭寫了我在大學聽到有個政治犯被拉出牢房,要被送去槍決前的情景(數十年後才知道是陳智雄先生)。我猶豫了兩天才決定寫,原因是,我很不願意將殘酷的情景寫出來,因為它可能會帶給不特定讀者不良的心理反應,比如感到恐怖等等。當年我聽到學長講後,從沒再轉述,一方面是當時根本不清楚到底怎麼一回事,好像是從某個大塊布中剪下一小方塊,完全沒有脈絡,不知從何說起;另一方面,如果它是真的,我反而也變得無法轉述,因為那是以會流血、會痛苦的人的身體去承受的,我如何講?在那不曾和人分享的三十餘年中,我有時會突然想起來,感到一種莫名的悸動。
最後,我還是決定寫,因為媒體已經有公開的報導,有些描述更graphic,我想我的臉書朋友大都已成年,或許不用考慮太多。貼出後,其實還是有點忐忑不安。世界上很多事情,如果我們想到是以和我們一樣的血肉之驅去承受的,其實很難當作一件「事」來巨細靡遺地予以刻畫。
貼文的那一天(05/30),也是泰源事件五位政治犯被槍決的日子。從二月底到五月底,戰後臺灣歷史有太多的死亡。我個人數字感很弱,雖說是歷史老師,年代、日期、數目常記不住,上課要靠小抄。以下只是我大概記得住,或簡單可檢索到的死亡:
二月:2/27緝菸事件中青年陳文溪被亂彈擊中,次日死亡。
2/28 林義雄律師的母親和雙胞胎小姐妹被殺害。
三月:3/06 三月屠殺的先聲:高雄市民代表到壽山和彭孟緝談判,遭逮捕;軍隊開始掃蕩市區,市民和學生死傷無數。遭逮捕的凃光明、范滄榕、曾豐明於8日遭槍決,林界於21日遭槍決。
3/08軍隊上岸後開始進行屠殺,無數年輕人和學生罹難,他們是「無名」的,那些為他們流淚的父母早已死亡,就算有手足,也大都不在人間了,再過幾年,相信已沒有人記得他們。接下來的幾天,本地菁英很多遭到殺害,他們有些屍骨無存,如林茂生、王添灯、施江南、阮朝日……等。
3/13湯德章(槍決)。
3/25陳澄波、盧鈵欽、潘木枝、柯麟遭槍決。但是,請注意,我們不能只看這四人,實際上代表市民到水上機場談判的意見領袖有十六人被逮捕,分三批槍決:03/18陳復志;03/23是吳溪水、陳陣、盧鎰等十一人。(慟哉,我們嘉義的菁英!)
四月:4/04 張七郎父子三人(被殺害)。
4/07 鄭南榕(自焚)。
4/17 泰雅族林瑞昌、高澤照,以及鄒族高一生、湯守仁、方義仲、汪清山六人(槍決)。
五月:5/19 詹益樺(自焚)。
5/20 許昭榮(自焚)。
5/28 陳智雄(槍決)。
5/30 鄭金河、陳良、詹天增、江炳興、謝東榮五人(槍決)。
今年4/22林義雄先生為「落實民主 停建核四」的訴求開始絕食。林先生的意志力,只要稍稍認識他的人都確信無疑。但,馬首是瞻的中國國民黨顯然是撼不動的(您看到此刻還想推服貿!),到了第六天,大家的焦慮變深了。戰後臺灣歷史已經有太多死亡了,我祈求上蒼:五月不要再有死亡。我無法想像,以後我們在五月還要再加上一個傷慟的紀念日。4/27我和三位學生南下,參加在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舉行的「鄒族原住民菁英受難六十週年紀念座談會暨音樂會」,這次很特別的是,第一次,第一次喔,舉辦受難鄒族菁英的共同紀念會,過去主要以高一生先生為主。您要知道:要受難者家屬站出來從來不是容易的事。四位鄒族領袖的受難日其實是4/17,可能為配合週末,主辦單位選在4/27舉辦。在返回臺北的車上,從臉書上看到忠孝西路已經被大批民眾占領,我的一位學生急著一下車就要和朋友會合。當時,我一直在想:如果林先生真的為反核奉獻了生命,我相信臺灣一定會暴動,那麼,我會去參加嗎?應該會吧!
所以當4/30得知林先生已結束絕食,我不由得流下淚來。是的,五月不會再添一個紀念日;是的,我不用為是否要參加暴動而天人交戰。我的同仁吳展良教授在臉書寫道:「為了不讓臺灣陷入撕裂與動亂,林先生做出了不起的決定。死生對他早已不算什麼,為了臺灣人民,冒著被人譏笑的危險,他毅然打消犧牲的壯志,這才是更困難的。我深深感到,因其無私的胸懷與愛人愛鄉土的性格,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。」(Chan-liang Wu:2014/05/01)吳老師講得很好。沒錯,那是了不得的決定,而且冒著被人譏笑的危險。您說沒有人在背後譏笑他嗎?當然有,郝柏村先生就公開講:「一個人喝了幾天開水,不吃飯,就把花了30年的時間及3千億經費,完成了99%的重大工程,停工封存,這不是街頭決策嗎?這不是民主的正軌。」
總之,過了五月,感覺或許可以輕鬆一點,但接下來是六四。雖然不是發生在臺灣,但站在普世人權的價值上,以及冀望對岸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的立場上,我們對六四感同深受。我們支持中國維權人士,除了更加深化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,也是一種普世關懷和精神的實踐。離我們很遠的圖博(西藏),每一個自焚的圖博人,都牽動我們的心。如果哪一天圖博能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,那麼,那些死亡的日子大概要填滿十二個月份吧。
過了六月,很快就七月了,然後7/03就是陳文成被發現被迫突然結束短短三十一歲的人生的日子!然後,7/24是臺南女兒施水環、丁窈窕被槍決的日子啊。真正認識她兩人,看過她們一顰一笑的人,在人間也剩不多了,終有一天,再也沒有人曾「有溫度地」記得她兩人了。那麼,新竹女中的傅如芝又死在哪一天呢?她和其他十一位同時被槍決的年輕人呢?啊,是一月!然後,八月是江國慶,才二十一歲。誰能告訴我們:有哪個月份,以公帑發射的子彈沒奪走無辜的青春和生命?
六四將近時,臉書有不少人在轉傳一個算術題:64+25,沒給答案。加起來剛好89,既指六四發生在1989,也標明六四到今年滿25年,也就是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了。我們要如何去想這25年呢?
中國的六四和臺灣的二二八,起因和經過很不一樣,也發生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,不過,若就事後統治集團的作法,倒有一些相同的地方。首先,血腥鎮壓之後,事件成了政治上最禁忌的禁忌,彷彿沒發生過。馬奎斯曾在小說《百年的孤寂》中描寫一個事件:在某個大屠殺之後,三千餘具屍體被火車載走,現場經過一場大雨的清洗,了無痕跡,唯一的倖存者不斷被告知:這裡沒有任何死亡。這裡沒有任何死亡。二二八在臺灣社會被完全噤聲,六四在中國也是如此,到現在一點也都不放鬆。君不見,日前賴清德市長在復旦大學講臺獨和六四,臺獨可以曝光,六四就被消音了。
我有時在想:研究歷史的人真的能「立體地」了解過去嗎?歷史涉及的是時間的進程,而這個進程是由不同年齡層,且「日日」會成長或衰老的人所「充實」而來的。也就是說,人,才是經歷時間的實體。在這裡,為了簡化問題,我們還得暫時擱置空間的因素,把它設想成在同個大空間中的時間的經過。這個時間中的「人」的變化,是我們必要處理的。其實不是很容易。比如說,二二八發生在1947年,那麼228+25等於多少?代表時間來到了1972年,它和64+25是等距的。我們必須想像:那些生在1947年的嬰兒,到了1972年,已經25歲了,但是他們絕大多數──絕大多數喔,從來沒有聽過二二八,而且徹底接受黨國教育,那可是貨真價實的中華民族主義教育,而且他們唯一認識的「蔣總統」就是蔣總統,是民族的救星。而在1972的這個時點,一切密不透風,距離1987年解嚴,也還15年──即使黨外人士,恐怕也無法想像真有解嚴的一天;吳濁流先生在《臺灣連翹》中寫道:「這戒嚴令已經有二十五年,到如今猶未解除,想來是會繼續到光復大陸吧。」臺灣戒嚴在1949,這裡的25年是1974。這句話出現在該書未發表的第13章,吳老自認為第9至14章在他生前無法發表。我個人在1981年出國讀書,當時我也無法想像臺灣有一天能解嚴。
在這裡,我們以出生二二八那一年的嬰兒為例,其實,事件發生時五歲以下的孩童,成長歷程大約等同二二八嬰兒,但容許我簡化這個圖景。這些25歲的年輕人是整個世代,然後,在他們之後每年還有無數的嬰兒不斷出生,他們構成了接受完整黨國教育的人口。如果我們拿這個等距來想像六四之後,在中國出生的龐大人口。你能期待他們腦中有六四?就算偶爾聽到,也很難黏著到腦海中已被塞得滿滿的各種「知識」。您說,他們會擁護現存體制,還是反它?更何況現在的中國,可是「大國崛起」!
讓人民無知是獨裁統治的根基。再來就是「排除懲治vs.馴化獎賞」原則了。二二八之後,臺灣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,就是統治集團以國家機器(軍警情治+司法),將對其統治有害,以及可能有害的分子排出社會,並予以懲處,從槍決、無期徒刑、十數年徒刑……到感化。六四之後,中共政權對六四關係者,以及維權人士的迫害,也是採取排除和懲治的方式,細節我們就不講了。
請記住:在這25年中,龐大的人口,在對國家暴力殘害異議者的無知中成長,接受體制的滋養,思想被馴化到不會也不可能「逾矩」,那麼,他不會覺得有何不自由,反而能充分享受體制所給予個人發展的機會。而且,體制內總會有一批人一路成功地擠上菁英輸送帶,最後躋身黨政商權貴集團,享盡各種好處。您說,他會更加支持體制,還是反對它?
不管極權統治,或專制獨裁政權,都具有自我鞏固的強烈本能和機制,它一面獎賞擁護體制的人,一面懲罰反抗體制的人,而且,就人口比例來說,前者一定遠遠高於後者。如果我們把獎賞和處罰的對象想像成被一堵高牆分成兩個世界,或許可以幫助我們以意象來掌握複雜的現象。姑且讓我們把兩個世界分別稱之為「牆內」和「牆外」吧。在牆內的人,當然有一些人不願遺忘血腥鎮壓,甚至起而反抗而面臨被丟到牆外的危機;但絕大多數的人會選擇遺忘,而新生代就是沒有記憶,或更正確地說,無法有記憶。牆外大約有兩批人,一批被迫流亡,一批是被丟出來的,具體來說,被丟到牢獄,遭到慘無人道的待遇。流亡的人,喊再大聲,撼不動高牆的一塊磚;在監獄受盡折磨的人,牆內的人絕大多數不知道他們的存在,遑論同情了。
六四前後,剛好有兩個牆內牆外的例子,反差之大,令人難過。我想絕大多數在中國牆內的人沒聽過李旺陽(1950-2012)吧?他是湖南工運領袖,支持六四民運,入過兩次長獄,總共被關22年。他在監獄中遭受慘無人道的摧殘,導致雙目失明,雙耳失聰。六四時,他高大健壯,2011年出獄時變成重度殘障的衰弱老人。2012年5月22日,他秘密接受香港有線電視訪問時,被問道:「你後悔嗎?」他的回答說,天安門的學生,「他們都流了血,他們都犧牲了。而我不過是坐牢,還沒有到砍頭。就算砍頭我也不後悔。」6月2日影片播出後,6日他被發現死在醫院,親友認為他「被自殺」。(可參考曹長青,〈誰說中國沒英雄?〉http://www.ntdtv.com/xtr/b5/2014/06/13/a1116026.html)
李旺陽專訪:六四二十三年至死不悔 http://youtu.be/gIBDQZbHicI
關於李旺陽疑似「被自殺」的報導: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8xTL9GShs0
那麼,讓我們來看看如果你合作的話,會有多大的不同。六四民運時,中國北京大學學生會的主席是蕭建華,根據《紐約時報》的報導:「他從未與政府對抗,1989年6月的事件也未使其成為中國的『通缉要犯』。實際上,這些事件助推他躋身最富有的人士之列。在那個動蕩的春天,蕭建華曾簡單嘗試在校方面前代表學生,隨後轉變立場,同意校方關於街頭抗議活動已然失控的看法。當時認識蕭建華的人表示,他甚至還與校方合作,試圖在軍隊進入北京,展開武力鎮壓之前平息抗議活動。獎賞很快來臨。甫一畢業,……」獎賞的內容,以及他現在擁有多少財產和資源,這些其實超乎我的生活經驗和想像,請讀者自行閱讀。倒是不管怎樣賺來的錢,大家都要呢,據報導:「蕭建華已經向中國兩大高校─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──共捐贈了3億元人民幣。最近,他還承諾向哈佛大學(Harvard University)捐贈1000萬美元。這所大學,正好就是王丹在中國服刑後,流亡美國期間獲得博士學位的地方。」(紐約時報中文網〈蕭建華,六四後起家的億萬富翁〉http://cn.nytimes.com/china/20140604/c04elite/)
李旺陽和蕭建華,多麼尖銳、強烈的對比!這都是發生在過去這25年內的事情。賞與罰,就是集權/專制/獨裁政體之所以能維持很長一段時期的主要原因;即使倒臺,舊勢力和它的支持者仍在,隨時伺機再起。您想想:當牆外的人用生命、青春,衝撞體制,牆內的人毫無所悉,兀自追求體制內個人的成功和幸福。哪一天牆真的倒了,他們還會認為是統治者開明的恩賜──哪有可能是那些顛覆國家的叛亂分子帶來的!惡人怎會帶來好事?然後,在自由民主化的新社會,擁有龐大資產和資源的舊勢力仍然是社會最大的力量,它的支持者遍布各地,而且位居要津。這就是此刻我們在臺灣所面臨的困境。
六四到現在25年,臺灣從二二八到稱得上自由民主化,要到1992年,也就是228+45(或1947+45)。四十五年是很長的時間。如果您生在1947年,到了1987年,您已經40歲了,然後,在1987到1992之間政治‧社會運動最劇烈的五年,您安安全全地站在原來的高牆這邊,之後民主化了,大家一起享受自由社會的好處,您毫無損失,甚至更好,因為在牆內的日子已經讓您成為人上人了。作為這樣的您,相信很難了解我們的社會曾經有過殘酷的牆外世界吧?您也不會認為過去有個高牆有何不好吧?它保障了社會的安穩,讓像您這樣的人可以全力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。而「人不為己,天誅地滅」不正是祖宗的遺訓?
如果以臺灣為鏡,64+25,中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。而我們自己的路,也還很長。臺灣的45年或67年牽涉到整整兩個世代,光是人口結構所形成的阻力就很難突破。幸好,三一八學運的年輕人,讓我們看到島嶼天光的可能。路阻且長,是必然的,我們不能輕估局勢;可慶幸的是,三一八召喚出幾乎是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──真正的新臺灣人,我們在這個世代身上,看到勇氣、承擔,關懷弱勢的心,以及重視分配正義甚於經濟發展的新思維。於是,我們看見了希望。
死亡的月份終會過去,因為他們都將活在島嶼的新生命中,在人們的記憶中,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(koh-o̍ah)。這也是我們唯一能給他們的東西,比起他們的生命和青春,何其微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