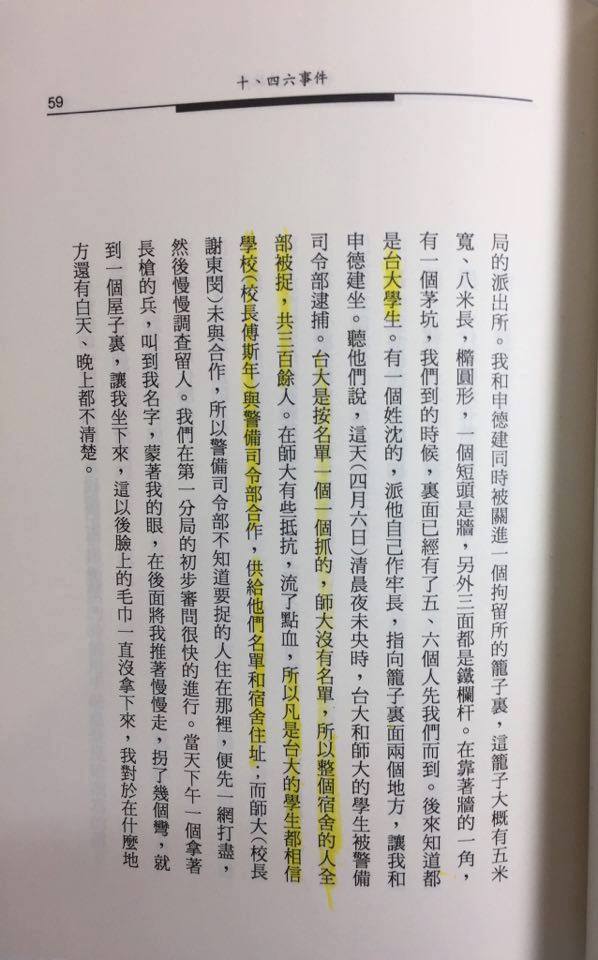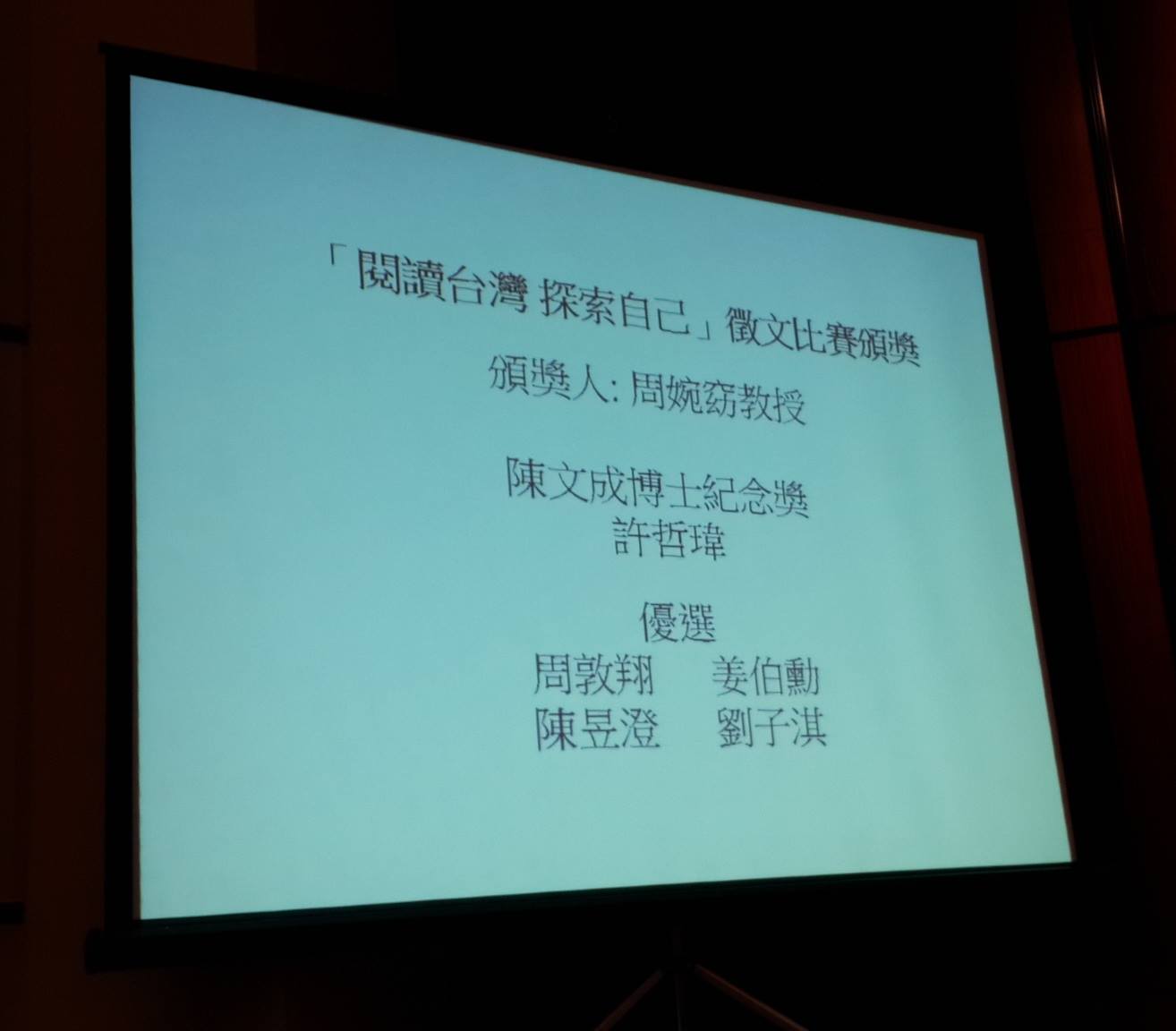「歷史很難!」(三)
貼出二篇「歷史很難!」小文,頗有些回饋。將來有可能陸續寫點我對歷史學的看法,和大家分享。
歷史確實很難,不過,也有它的優勢,有時比我們了解周邊正在發生的事情更容易。首先,研究過去,必須窮盡史料,如果有檔案就要看檔案,有還能訪談的就要訪談,那是一個「鳥瞰」式的全觀點,有時也能自由地揭開重重密幕,看到事情背後的操手──抓到藏鏡人(們),釐清事件的來龍去脈,得到一個比較全面和接近真相的理解。反觀處在事件中的當代人,其實是沒有這種優勢的。
歷史研究者可以「閒閒地」翻看檔案,將「過往事件」的參與者脈絡化,比如為何A(A們)要這樣講,為何B(B們)有這樣的大動作,C(C們)是公報私仇等等,然後在一片刀光劍影中有人借力使力、借刀殺人;這些當代人不是一定看不出來,在網路發達的時代只要上網搜尋,大概就可以了解個大概,至少表面那一層。但是,大家士農工商,各忙各的,只能從主流媒體吸收(或被餵養)消息,即使有人知道真實情況,也沒有管道講出來,而且很多事情在「當下」講出來是有顧忌或要挨告的。在這裡,我們看到「大眾vs.小眾」的問題,很小很小的小眾知道真相,但只要能影響很大很大的大眾,就能顛倒黑白,混淆是非。
然後,post-事件的歷史研究者的您,「閒閒地」在紛雜的檔案中,發現真實比虛構更離奇複雜,並「抓到」背後的操控之手;你也有機會訪問當時知悉內情的人,他們當時無法講,「事過境遷」已無大礙。於是,您拍案大呼:哇賽,竟然是這麼一回事!然後,您覺得很奇怪,事情這麼大條為何事件當時的人都毫無所覺?然後,細心如您去翻閱當時的報導,發現是有幾則小小消息有暗示到,但實在太小則了,淹沒在排山倒海的反向訊息中,怪不得沒人注意。當然,當年的小眾是有人明白的,只是小眾畢竟就是小眾。
您將這些資料整理好,也許寫一篇擲地有聲的論文,也許是一本容易讀、好讀的小書。您的讀者看得很痛快,拍案叫絕,原來當年的事件是這麼一回事!但往事已成灰,若有死人,人也死了,然後,大家各自士農工商去,在自己所身處的時空中繼續在迷霧中行進,以為很知道自己的時代。
所以,歷史確實很難,但了解當代未必比較容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