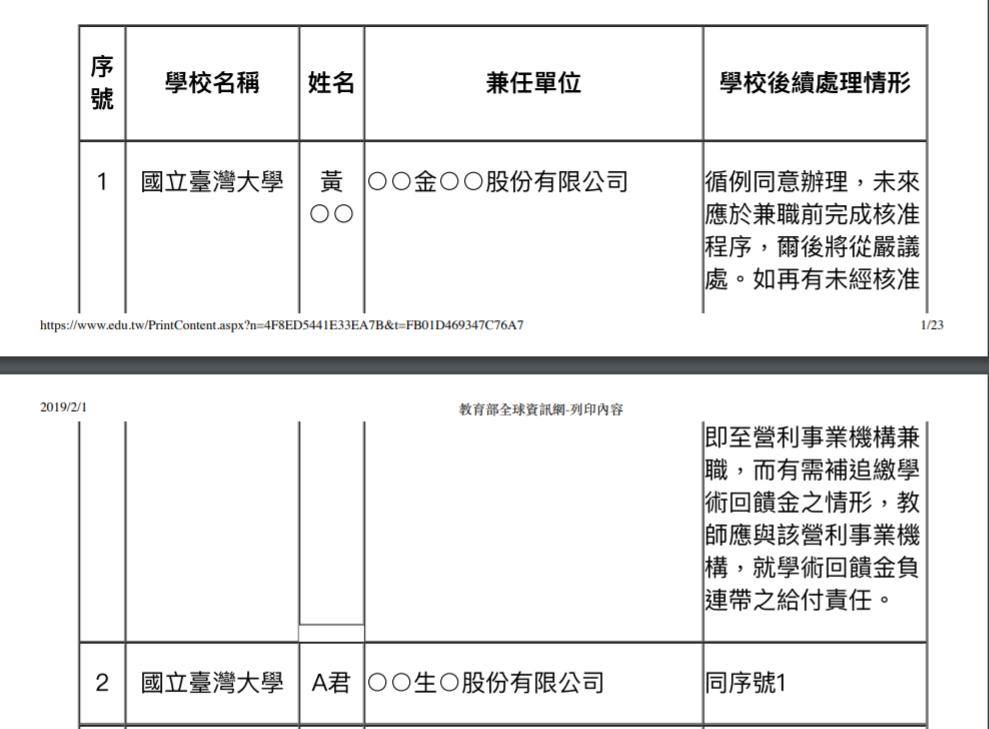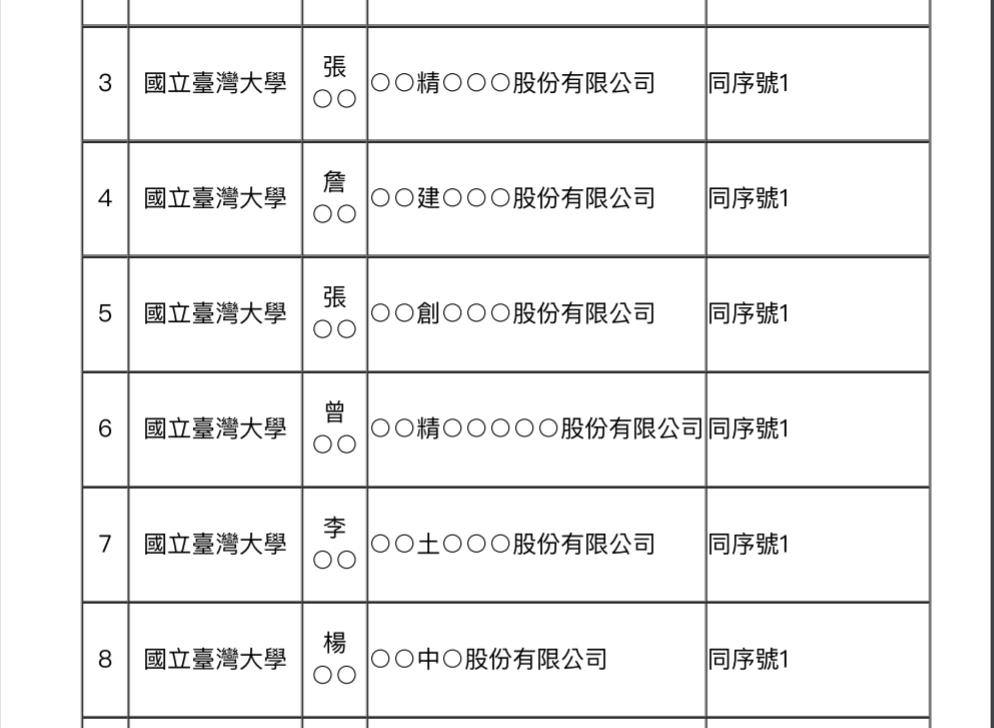分享文章:中央社 2019 02 20 報導
李喬老師有一本小說叫作《咒之環》。
作為台灣史研究者,我認為「國共問題」,在歷史上和台灣並沒關係,但戰後的台灣卻陷入了這個「咒之環」。請問:1945年之前,國共慘烈血腥的鬥爭,以及兩次的「國共合作」,和台灣有什麼關係?為何我們今天還要被國共第三度合作綁架呢?何時我們才能爭脫這被強加、且被黨國教育成理所當然的「咒之環」呢?
引文:
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姜皇池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,協定、條約是國家與國家簽署、以國際法作為規範的文件,協議則是國內法文件,不適用國際法。從法律觀點來看,「和平協議」某種程度而言是屬於國內交戰團體的文件。
……他表示,基本上如果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也就表示,台灣的執政者承認台灣跟中國目前的狀態是早期中國內戰的延續,並藉由一個和平協議來終止這樣的戰爭狀態,也就等於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
……若兩岸簽署和平協議,在此狀況下,就國際法而言,其他國家就不能干涉所謂「中國的內政」。
……若台灣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,所造成的法律意義就是,美國出售武器台灣是違反國際法的做法。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這不就很「傷重」(台語)阿?
(ㄟ姜老師的照片未免太年輕了,哈哈)
文章連結:中央社 2019 02 20 報導